]王文娟的黛玉焚稿,唱腔清雅婉转,韵味醇厚。对黛玉的性格构思,逻辑严密,表演细腻准确,真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看她全心全意地投入角色的表演,几疑舞台即是潇湘馆。
大导演李翰祥(1926年4月18日-1996年12月17日),曾师从画家徐悲鸿,后进入电影公司,最终成为一代名导。他以《貂蝉》、《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作品引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港台黄梅调电影潮流,又为台湾电影的崛起培养了不少了新人演员、导演。1980年代,李翰祥来到内地,拍摄了《火烧园》、《垂帘听政》,成为第一位获准进入故宫实地取景拍摄的导演。
公映于1977年的《金玉良缘红楼梦》,在李翰祥的作品中并非上乘,但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熏陶的他,把这部名著搬上银幕,一改当时港台地区盛行的、粗糙的红楼改编之风。而在开拍初,李翰祥临时把林青霞、张艾嘉的角色互换,也发掘了林青霞后来的反串潜力。在《金玉良缘红楼梦》之前,李翰祥曾有过两次改编《红楼梦》的机会,却都被他了。这是为什么?
刚刚过去的2016年,是李翰祥诞辰90周年、逝世20周年,他的回忆录《三十年细说从头》由后浪出版公司于近日首次在内地出版。书中,他细说从头,各种影坛掌故、民俗文化都有。关于《红楼梦》电影的改编,也有详细述及,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相关部分。

其实,在我拍林青霞与张艾嘉的《金玉良缘红楼梦》之前,有两次可以导演《红楼梦》的机会,都叫我推掉了。第一次是上海越剧团到演出的时候,表演剧目中以徐玉兰、王文娟的《红楼梦》为主,金采风的《碧玉簪》及吕瑞英的《打金枝》(即《金枝玉叶》)为副。当时的演出相当轰动。我是标准戏迷,除了对广东大戏的粤曲听不大懂之外,其他任何剧种和曲艺,都是每演必到的。绍兴戏和评弹本来也听不大懂,不过有一位杭州老婆做翻译,听上几遍之后,也就全部了然了。看《红楼梦》的时候,对徐玉兰和王文娟她们两位的表演愈看愈过瘾,唱腔越听越入迷。本来对徐玉兰一出场还有些不能接受,总觉得宝玉胖了些,年龄也实在太大了些,可是一场三摔玉表演下来,这些缺点全忘得一干二净,觉得她就是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她的唱腔旋律优美,有时刚劲、挺拔,有时委婉、柔和;哭灵时一声悲切而哀怨的“林妹妹我来迟了!”动弦,感人肺腑,底下的“想当初你初到我家来”的一大段清板,娓娓唱来,如珠落银盘,顿挫显著,明暗清晰。普庆,静得连隔邻观众的呼吸声都听得到。

王文娟的黛玉焚稿,唱腔清雅婉转,韵味醇厚。对黛玉的性格构思,逻辑严密,表演细腻准确,真可以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看她全心全意地投入角色的表演,几疑舞台即是潇湘馆。
黛玉葬花和焚稿时都有若隐若现的暗泣,紫鹃在黛玉归天后的一声“姑娘”,和宝玉哭灵时的一声“林妹妹”之后,都有喊地呼天地号啕大哭,她们几位都能表演得恰如其时、恰如其分。

生活中的哭,是从悲中来,难以,很自然地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了起来,绝对想不到也顾不到姿态音韵美不美、妙不妙。可是舞台上的哭是通过了技巧的表演,非但要哭得真,更要哭得美,还要边哭边唱;唱又要分得清,轻重听得明,感情激动时,如江河一泻千里,但山回转,当急则急,当缓则缓;调门儿也有时高可入云,有时又低沉海底,调门高,固然难度大,但调门低,有时更不好唱,徐玉兰哭灵时的“如今是,千呼万唤唤不归”的“归”字,和王文娟焚稿时的“我一生与诗书作了闺中伴”的“伴”字,一高一低,她们两位的抑扬顿挫,都恰到好处,不温不火。
黛玉归天前,耳闻喜乐,锣鼓喧天,迷蒙间仿佛看见宝玉前来,一句:“宝玉……你好……”然后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你好”的下面也许是千言万语道不尽的,如今省略处不嫌其简,正如中国画讲究,“藏”和“露”的道理一样。所谓“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省略是要表现更高的艺术境界。“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这余味是无穷无尽的!
看过戏回家,彻夜难眠,我真希望把这一台戏搬上银幕。那时我刚拍过《貂蝉》和《江山美人》,成绩都还差强人意,尤以《江山美人》,是打破了历来国片票房纪录的。那时新华戏院重建新张,票房的长龙居然由弥敦道绕过邵氏大厦的,整整围了一圈儿,是直至新华再拆除之前重未再有过的现象。所以很多人对我拍古装歌唱片还比较有信心,但怎么也想不到,凤凰公司的导演朱石麟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是请我和翠英吃饭,并且知道我看过几遍越剧《红楼梦》,所以也约了徐玉兰和王文娟!
和朱石麟先生在永华公司分手之后,多少年来因为左了右了的关系,一直就没有见过面。我和翠英商量了一下,她认为也许朱先生希望知道我对《红楼梦》(越剧)的观后感,只是大家对艺术方面交换交换意见而已,不会有任何成分在内的。尤其朱先生是老前辈,却之不恭,于是我们如期赴约。
遗憾的是那天徐玉兰因为感冒的关系未能和王文娟一道来,不过翠英认为看看的林妹妹也应该知足了。她丝毫没有化妆,看惯了女士的描眉画鬓,蓝眼圈,红嘴唇,反倒觉得她格外地淡雅宜人。王文娟一直不大讲话,我则是一向口没遮拦,发表欲强烈得很,朱石麟先生在恰当的时候也说些对越剧团的意见,怎么也想不到朱先生忽然问我:“有没有兴趣把《红楼梦》搬上银幕,来一个舞台艺术片怎么样?”我乍听之下还真是一愕,半天不知如何对答才好。虽然知道那时凤凰公司出品的片子,星马版权大部分是邵氏兄弟公司发行的,但在制片方面,倒从来没有公开合作过。虽然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本身没有什么成分,但凤凰总算一家公司,如果合作起来,不只台湾的上映有了问题,甚至于会牵一发动地引起其他不必要的麻烦。
也许朱先生明了我久久不出声的道理,他想出了个折中的办法,说是可以由我和胡小峰联合导演,我只是做幕后的策划工作。虽然如此,我仍因邵氏的合约关系,事前一定要取得六先生的同意,朱石麟先生倒也认为是应该的。
饭后王文娟先走,留下我们夫妇,和朱先生随便谈了些越剧团在港上演的盛况,然后也谈到徐玉兰和王文娟两位在舞台上的造诣。我忽然想到,刚才吃饭的时候,发现王文娟好像是镶了两个金牙齿,在舞台上,观众距离远,倒也看不清楚,但在银幕上的大特写,一定会看得一清二楚,林黛玉镶着两个金牙总不大对味儿。朱先生认为这是很容易处理的,最多重新装过。我把这次谈话和邵逸夫先生讲过之后,他没说什么,只是笑着摇了摇头。所以,虽然我也出席过廖一原、胡小峰和韩雄飞几位先生在普庆楼上的高华酒楼举行的初步研讨拍摄《红楼梦》的座谈,但我始终没参与红片的幕前幕后工作。
事后知道《红楼梦》在清水湾片厂搭景拍了一个多月,因为徐王两位对于布景、服装等等的不满意,就停了下来,回到上海之后又重新拍摄,导演也换了《清宫秘史》的副导演岑范。
这就是金汉在台湾对新闻界大声疾呼地说是抄袭的样本。至于这件事的内情他当然不知道,因为那时凌波还以小娟的名义,在演厦门戏。而金汉还没有参加电影界。
邵氏公司第一次筹备拍摄《红楼梦》的时候,举止很神秘,大概是当时的制片主任的意思吧。我到日本京都的今津区,拍摄《杨贵妃》《王昭君》《武则天》三部影片之前,只听说袁秋枫要拍一部古装歌唱片叫《秋凤》的,并没有要拍《红楼梦》,一直到我们的外景队出发了,才开始收唱歌,搭布景。我还是在日本看到由家中寄去的,才知道乐蒂演林黛玉,任洁演贾宝玉,幕后代唱的是静婷和厦语片的小娟。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故世近两百年,不会向任何人把它搬上银幕的制片公司追究版权,也没有任何公司和任何人取得专利,所以谁都可以把它改编成电影。虽然我曾向公司提出拍摄《红楼梦》的计划,但制片大可以名正言顺地告诉我其他影片尚未结束,已经交给别的导演拍摄,为什么如此这般的呢?实在令人费解!
一直到我离开邵氏公司之后才了然,原来这是有人长远计划的迫虎跳墙第一招。因为当时我在邵氏上得老板信任,下受同人爱戴,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到后来几乎整个邵氏的摄影棚排期,都是由我策划(迄今的排期表,仍是我设计的那一张)。同时开拍的四组黄梅调影片(王月汀的《西厢记》、高立的《凤还巢》、何梦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胡金铨的《玉堂春》),都挂着我联合导演的名义。树大招风,所以,早有一小圈子人,在暗中使劲儿,伺机而动,所以我说《红楼梦》的开拍,是他们乘虚而入,声东击西的第一招。
我一向处人行事,都是明来明往,心里绝对存不下话,直言谈相,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什么夹带藏掖。两点之间,不是以直线为最短吗?那么何必曲曲弯弯?
等我由日本回来,袁秋枫的《红楼梦》已经开始拍摄。秋枫倒是很虚心地到我住的加多利山道的山景大厦,来过几次,就个人对《红楼梦》的看法,提出一些问题来讨论,等戏拍完之后倒也约请看了。据说六先生并不满意,所以由张彻兄提出一些补戏的意见,把金钏跳井的戏重新拍过(那时张彻只是邵氏的编剧,还没开始导演工作)。
我第二次推却拍《红楼梦》的机会是我由台返港,重新加入邵氏公司的时候。签好两年的导演合约之后,六先生希望我第一部戏先拍黄梅调的《红楼梦》,原因是岳老爷筹备了一阵,唱歌也收了一部分,饰演贾宝玉的人选也决定了凌波,他认为黄梅调是我的拿手好戏,凌波又是老搭档,驾轻就熟,理应事半功倍。但是我认为不然。
理由是我以前拍黄梅调影片,在收唱歌之前已经有了拍摄时的预想,别人收的唱歌,对我是不适用的;而凌波饰演宝玉的年龄,无论如何大了一些。而我那时刚看过《殉情记》,印象犹深,我说我如果拍《红楼梦》,也希望以《殉情记》的方法拍摄,所以剧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年龄不应与原著脱离太远。

很多人的错觉,黛玉进府时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其实那时她只不过是六岁的孩子,与混迹在内帏的贾宝玉是儿时的伴侣,一个是贵族阶级的少女,一个是“诗礼簪缨之族”的公子哥儿。电影不像舞台剧,盖叫天八十多岁一样粉墨登场演二十多岁的武松,尽管功架如何了得,举手投足依然虎虎生风,可是通过银幕上的大特写,岂不要叫观众吓一跳,还以为哪里来了个老太监!
在曹雪芹虚构的大观园的艺术境界里,贾宝玉自幼就生活在父亲贾政和祖母的矛盾中。父亲希望他被教养成贵族阶级的孝子,立身扬名,不皇恩祖德;祖母却一味地娇养、宠爱,一日不见都不欢心的心肝宝贝儿!所以把他娇养在内帏,以逃脱贾政的。于是宝玉在姐姐妹妹表姐表妹的一群少女和一群丫鬟婆子中间长大,使他产生了对所谓“男子”的轻蔑和,得出了完全违反“男尊女卑”的封建秩序的结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山川日月之精秀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这当然是一种十分含混的阶级观点的思想。
贾宝玉的这种愤慨和不满,导致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否定:他厌恶贵族阶级的繁文缛节,厌恶僵死的礼教,厌恶他父亲他努力追求的那种“经济”;他把专门奔走、猎利禄的人们骂为“禄蠹”;他无心于封建文人的必定之的科举制度。用现在的说法,那应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逆性格。
所以,我认为演古典文学中的贾宝玉,和坊间传说的民间故事梁山伯完全是两回事。梁山伯只要演出他的憨直、诚恳就可以胜任了,而演贾宝玉就要复杂得多。虽然演员并不一定是红学专家,像周汝昌先生所说的去研究什么内学、外学,但起码要看过《红楼梦》,了解一下贾宝玉和贾宝玉的生活,这当然不算苛求,但已非一般演员所能做得到的了。
虽然如今在国内外出了千百位研究红学的专家,出过了多少部所谓“内学”“外学”的专论,加上了各种版本,和以前的莫名其妙索隐,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尽管有些还算不错的评弹、戏曲,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完美的《红楼梦》电影。
我不喜欢一贯的扭扭捏捏地捂着半拉充整个的假式的《红楼梦》(一般舞台剧,以及袁秋枫和我所拍的形式),也不喜欢粗俗地描写大观园生活的《红楼梦》(像邵氏的《红楼春上春》)。我认为应该用真正于原著的子,拍一部属于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

当然一部影片的篇幅是有限的,可以分成:“太虚幻境”“王熙凤大闹宁国府”“红楼二尤”“晴雯”“史湘云”“妙玉”……
从来没有人拍这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也是因画中的“藏”和“露”的问题:“藏”得太多到喉不到胃,“露”得太多又难免流于粗俗。也没有人拍过贾宝玉的同性恋的倾向。至于焦大口中的:“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真情实景,更是很难直言谈相的。但是怎样才能把荣宁二府溃烂的面貌里,男女混乱的关系,通过电影语言描写出来呢?
因为贾宝玉、林黛玉是在这样中成长的,不细心准确地描写出他们周围的境况,怎样描写宝玉愤慨不满的叛逆性格?又何以解释黛玉的狭窄、小气、爱哭,无缘无故发小姐脾气,而令自己孤立,使别人反感?
这一切都因为他们荣宁二府在膏粱锦绣生活的外衣下,挥霍无度,。大观园里的流水都是的,所以黛玉才要为落花安排一个花,才要在临死告诉紫鹃:“叫他们好歹送我回去,我的身子是干净的。”
这些话都是我不导《红楼梦》而改拍《大军阀》的原因。六先生和一起参与讨论的方逸华小姐,都同意了我的见解,暂时不拍《红楼梦》,但并没有放弃拍摄《红楼梦》的意愿。这也许就是后来同时拍了两部《红楼梦》(《金玉良缘红楼梦》和《红楼春上春》)的原因吧。也都不是我想象的《红楼梦》。如果说一部驴,另一部就叫非马吧。至于金导凌演的一部,因为没有看过,所以也不能妄加。不过后来因为我第三次的合约期满,有人想约我拍摄一部清末的文艺片,台湾一家公司委托江述凡先生和我谈台湾版权问题,因而知道了两部《红楼梦》在台湾打对台的内幕。

李翰祥最终执导了《金玉良缘红楼梦》,由林青霞扮演贾宝玉、张艾嘉出演林黛玉,当时两人都只是参加过表演培训班的无名小辈。
到现在还有人用“两部红楼梦,在台湾展开骂战”,这是有意替金汉的《红楼梦》解释。以邵逸夫先生领导的邵氏公司宣传稿,一向倒是只宣传自己,即使别人家的宣传字眼直指着鼻子,他也不主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对金导凌演的《红楼梦》,更是如此。他们不只在宣传方面混淆黑白,并且地争取同情票,登广告启事要求邵氏的《红楼梦》等他们一起上,运用各种关系达到此一目的。
江述凡先生是参与金导的《红楼梦》宣传的,他告诉我他看过邵氏的《金玉良缘红楼梦》之后(用他的原词):“我看完了就傻了眼了,愣住了,马上回去就开了个会,告诉他们以戏比戏谈都不要谈,连门儿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吧!”
所谓想办法也者,什么办法?难道还有工夫补戏不成?当然是想一些高招,什么桥最好?汲取“哀兵必胜”的道理,说李翰祥以大压小,说邵氏以强凌弱。广告的词句已经到了泼妇骂街的程度。,单方面的骂街又怕引起观众反感,于是又做出来李翰祥骂金汉是“卖山东馒头的”,然后又博取山东人的同情,说了一些自编自导的话,也就使人觉得“双方骂阵”的原因。
当然无风不起浪,有一次在拍戏的时候,刚由台北回来的胡锦告诉我,刘维斌说:“金汉怎么那么傻,那么不自量力,那么多朋友劝都不听,一定要以卵投石,跟邵氏比,跟李翰祥比,你见过卖馒头的忽然出版一本书吧?”我当时连笑都不敢笑,也不置可否,怎么传到别人的耳里,又怎么变成了我的话,就要问编剧先生或者是小姐了!
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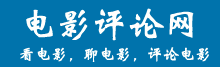




 删除。
删除。
网友评论 ()条 查看